余光中最惊艳短句
余光中最惊艳短句如下: 1、一个能思想的人应该乐于和自己为伍。 2、生活中能有人伴在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就应该感激。 3、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 4、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 5、只是到了夜里,人籁寂寂,天籁齐歇,像躺在一支坏了的表里,横听竖听,都没有声音。 6、白露为封面, 清霜作扉页,秋是一册成熟的诗选,翻动时满是瓜香与果香。 7、每当有人问起了行期,青青山色便梗塞在喉际。他日在对海,只怕这一片苍青,更将历历入我梦来。 8、当初发明阳台的人,一定是一位乐观外向的天才,才会突破家居的局限,把一个幻想的半岛推向户外,向山和海,向半空晚霞和一夜星斗。 9、浅蓝色的夜复溢进窗来夏斟得太满, 萤火虫的小宫灯做着梦。梦见唐宫梦见追逐的轻罗小扇, 梦见另一个夏夜一颗星的葬礼。梦见一闪光的伸延与消灭, 以及你的惊呼我的回顾和片刻的愀然无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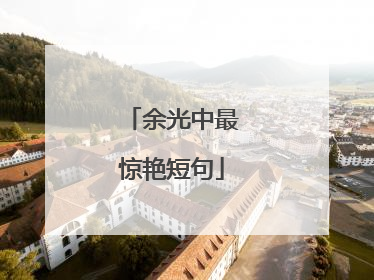
余光中最惊艳的情话
1、今生今世,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 是听你说的, 第二次你不会晓得 我说也没用, 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 有无穷无尽的笑声, 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三十年,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2、若逢新雪初霁,满月当空。下面平铺着皓影,上面流转着亮银。而你带笑地向我步来,月色与雪色之间,你是第三种绝色。 3、旅行之意义并不是告诉别人“这里我来过”。是一种改变。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在旅途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 4、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 5、云只开一个晴日,虹只驾一个黄昏, 莲只开一个夏季。 为你,当夏季死时,所有的莲都殉情。 6、步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像一首小令, 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 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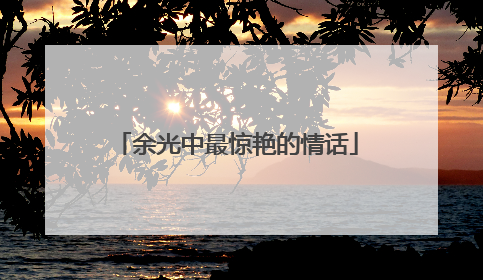
余光中诗文句子的赏析!!求赏析。
我慢慢意识到,我的乡愁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鹤发童颜的余光中在接受来自祖国大陆的记者采访时,又一次忘情地吟唱起他作于30年前的《乡愁》。 由于余光中15年前从香港返台后“背弃台北”而“转居高雄”,记者初抵台北欲寻访这位名播两岸的诗人的计划受到困扰。幸好报载他要到台北出席一个文学翻译界的笔会,我们相约于他,没想到诗人竟爽快地答应了。 采访自然是从他的创作谈起,而“乡愁”又是双方共同的话题,余光中告诉记者,中央电视台刚刚与他谈妥,将他的诗作《乡愁》谱曲后作为电视系列片《闽南名流世家》的主题曲,这部电视片讲述的是郑成功后人在海峡两岸生活的情况。 ■“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49年离开大陆,3年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先后在数所大学任教,创作,也曾到美国和香港求学、工作。目前在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已出版诗集、散文、评论和译著40余种,他自称是“文学创作上的多妻主义者”。文学大师梁实秋评价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从21岁负笈漂泊台岛,到小楼孤灯下怀乡的呢喃,直到往来于两岸间的探亲、观光、交流,萦绕在我心头的仍旧是挥之不去的乡愁。”谈到作品中永恒的怀乡情结和心路历程时他说,“不过我慢慢意识到,我的乡愁现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60年代起余光中创作了不少怀乡诗,其中便有人们争诵一时的“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白发盖着黑土,在最美最母亲的国土。”回忆起70年代初创作《乡愁》时的情景,余光中时而低首沉思,时而抬头远眺,似乎又在感念着当时的忧伤氛围。他说:“随着日子的流失愈多,我的怀乡之情便日重,在离开大陆整整20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一挥而就,仅用了20分钟便写出了《乡愁》。” 余光中说,这首诗是“蛮写实的”:小时候上寄宿学校,要与妈妈通信;婚后赴美读书,坐轮船返台;后来母亲去世,永失母爱。诗的前三句思念的都是女性,到最后一句我想到了大陆这个“大母亲”,于是意境和思路便豁然开朗,就有了“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一句。 余光中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紫金山风光、夫子庙雅韵早已渗入他的血脉;抗战中辗转于重庆读书,嘉陵江水、巴山野风又一次将他浸润。“我庆幸自己在离开大陆时已经21岁。我受过传统《四书》、《五经》的教育,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学的熏陶,中华文化已植根于心中。”余光中说,“如果乡愁只有纯粹的距离而没有沧桑,这种乡愁是单薄的。” 《乡愁》是台湾同胞、更是全体中国人共有的思乡曲,随后,台湾歌手杨弦将余光中的《乡愁》、《乡愁四韵》、《民歌》等8首诗谱曲传唱,并为大陆同胞所喜爱。余光中说:“给《乡愁四韵》和《乡愁》谱曲的音乐家不下半打,80多岁的王洛宾谱曲后曾自己边舞边唱,十分感人。诗比人先回乡,该是诗人最大的安慰。”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 1992年,余光中43年后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谈到这次对北京的访问,余光中说:“我的乡愁从此由浪漫阶段进入现实时期。我大陆之行的心情相当复杂,恍若梦中,我在北京登长城、游故宫,被两岸同胞的亲情所感染,写了不少诗作,尽情抒解怀乡之愁,因为原来并未到过北京,所以首次回大陆,乡愁并没有一种很对应的感觉和体验。” 自此以后,余光中往返大陆七八次,他回到了福建家乡,到了南京、湖南等地,在南京寻访金陵大学故地,在武汉遍闻满山丹桂,探亲访友,与大陆学子对谈,对大陆自然多了一层感知和了解。 他说:“初到大陆,所见所闻,令我兴奋不已。但我也看到洞庭湖变小了,苏州的小桥流水被污染了,这些让我也产生些许失望。但此后去大陆多次,那里的变化之快让我惊异和兴奋。”在四川,作家流沙河赠他一把折扇,问他是否乐不思蜀,他挥毫题字:思蜀而不乐。翰墨间仍飘出了淡淡的乡愁。 他说:“玄武湖,紫金山都变了,但大学原来的校舍我还能认得出来。我接触了许多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水平都不错。尤其是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心一意搞建设,魄力很大,又很踏实。” 余光中说,在大陆的游历也使他越来越发现,他的乡愁是对中华民族的眷恋与深情。“我后来在台湾写了很多诗,一会儿写李广、王昭君,一会儿写屈原、李白,一会儿写荆轲刺秦、夸父逐日。我突然意识到,这些都是我深厚‘中国情结’的表现。” 他说:“我在大陆大学演讲时朗诵我的诗《民歌》,‘传说北方有的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才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在场的学生和我一同应和,慷慨激昂,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感情。” 抗战时期,余光中随母亲逃出南京,日军在后面追赶,他们幸得脱险,后来辗转越南到了重庆。日军大肆轰炸重庆时,上千同胞受难,余光中幸好躲在重庆郊区。谈起这些浩劫,余光中说:“这些都激发起我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那时候,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豪情,只要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万里长城万里长’,都会不禁泪流满面。前几年在东北访问时,青年时的歌谣仍萦绕着我。于是写下了‘关外的长风吹着海外的白发,飘飘,像路边千里的白杨’的诗句。” 余光中承认,他的诗歌在赴美期间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摇滚乐的影响,比较注意节奏,因此也容易被作曲家看中谱曲,但他仍以“蓝墨水的上游是黄河”来表明他的文化传承中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说,尽管他在美国上过学,诗文中也受一些西方东西的影响,但不变的是中国文化的遗韵和对中华民族的怀思。他的作品深受《诗经》的影响,也学习过臧克家、徐志摩、郭沫若、钱钟书的作品。他说:“我以身为中国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为幸。” ■“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 余光中曾在文章中写道:“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他说:“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 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他说,中国文化对所有的“龙族”都有着无法摆脱和割舍的影响。谈到台湾一些人企图割裂两岸的文化联系,他说:“吃饭要用筷子,过端午节,过中秋节,能改得掉吗?大家所信仰的妈祖,不也是从大陆来的?余秋雨等大陆文化学者到台湾演讲引起轰动,不都说明中华文化是一脉相传的?” 余光中的妻子是他的表妹,江苏人,有着女性知识分子的韵味和气息。重庆时期,两人青梅竹马。他们至今都保留着一个特色,那就是在家的时候讲四川话。有次余光中到四川大学演讲,他征求校方,既然到了四川,是否就用四川话演讲,后来校方告诉他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就用普通话吧”,余光中因此没能有机会显示他讲四川话的才能。 从香港返台后,余光中为躲避繁琐的事务和各种交际,一直定居在高雄,在“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尽管年过七旬,但精神矍铄,幽默健谈,不失赤子之心。他每天坚持工作,上课、创作、编书,乐此不疲。他的近作不时被大陆报刊转载,一些大陆出版社要出他的作品集,他便不辞辛苦亲自校对。 “国立中山大学”环境优美,紧邻寿山风景区,南边是世界排名第四的货运港口高雄港,正西是西子湾,他的办公室就在面海的半山腰。余光中面海低语:“在台北时办公室也靠海,不过是靠着台湾东海岸,我看着太平洋有什么意思,看美国有什么意思。这也许是天意,现在我凭窗而立,便可直视海峡西面,尽管身在台湾,我可以眺望对面的香港,可以一生守望着我的大陆。”■文/赵新兵顾钱江 《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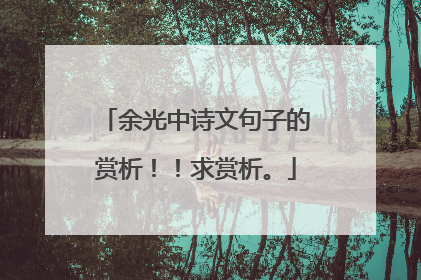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经典句子
1、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2、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 3、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提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 4、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 5、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枝叶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 6、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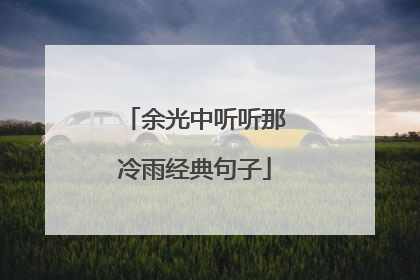
余光中有哪些绝美的诗句?
诗人余光中先生在高雄医院过世,享寿90,走完了他的这一生,余光中我们都不陌生,尤其是“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的绝美诗句。逝者已逝,我们沉痛的怀念,余光中先生,一路走好! 余光中一生留下不朽的著作,也揽获诸多奖项。他曾获得《吴三连文学奖》、《中国时报奖》、《金鼎奖》、《国家文艺奖》等台湾所有重要奖项,获得第十三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 下面我就为大家来说一下余光中的哪些绝美的诗句,让我们来领略一下大师的心声: 余光中的《新月和孤星》 我们记住了“像一只寂寞的鸥鸟,追着海上的帆船,像一只金色的蜜蜂 恋着清香的花瓣;也没有亲近的拥吻,只有深深的感受; 也没有海誓和山盟, 只有默默的厮守;直守到暗夜的尽头,望瘦了容光如许;才黯然地一同殉情,溺在黎明的光里”的深情! 《苍茫时刻》 “温柔的黄昏啊!唯美的黄昏, 当所有的眼睛都向西凝神,看落日在海葬之前,用满天壮丽的霞光, 像男高音为歌剧收场,向我们这世界说再见, 即使防波堤伸得再长,也挽留不了满海的余光, 更无法叫住孤独的货船,莫在这苍茫的时刻出港。”夕阳斜下的《苍茫时刻》那么美,也那么伤! 余光中曾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从母亲到外遇》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妻子是不一定的,更别说情人外遇,但母亲是无可替代的。 《寻李白》 树敌如林,世人皆欲杀 肝硬化怎杀得死你? 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在过人文采与幽默风趣之外,千帆过尽,离乡数十载、远在台湾的余光中始终牵挂的,终究是他的故土。每一首诗句都是大师在字里行间穿行的对祖国的不灭情愫。 《春天,遂想起》 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 喊我,在海峡这边 喊我,在海峡那边 喊,在江南,在江南 多寺的江南 多亭的江南 多风筝的江南啊 钟声里的江南 (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 多燕子的江南 总结: 余光中先生除了《乡愁》之外,有大量的遗世,而如今,巨匠已去,但他的诗文却仍饱含生命力。只愿他的殷殷话语,能带你过尽千帆、穿透迷雾,走进崭新的人生中。 下面再次让我们领略一下《乡愁》的魅力,去感受一下余光中老先生那永远的大陆心,病一次来缅怀余光中先生: 《乡愁》 作者: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余光中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先生殁了,89岁。过了米寿,不可谓不久。 朋友们都开始念叨《乡愁》: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大概因为写得两岸士子血肉连心,大概入选了语文课本之故。 小时候,或者是上课不用心,或者是语文课本无载,并不太记得这段诗。 所以我印象里的余光中先生,是另一个样子。 比如《寻李白》: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从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当地一弹挑起的回音 比如十一年前那首《草堂祭杜甫》: 七律森森与古柏争高把武侯祠仰望成汉阙万世香火供一表忠贞你的一柱至今未冷如此丞相才不愧如此诗人 比如《听听那冷雨》里,蒋捷爱好者一望而知的段落。 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比起《乡愁》来,这些诗大概更接近他的气质:用典故,用意象,抒情,怀古。 他强调的弹性,是对于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蓄、融合无间的适应能力,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基础,在情境所需时,也不妨用一些欧化或文言文的句子,以及适时而出的方言或俚语,或是穿插典故。文体和语气变化多,散文弹性当然越大, 发展的可能性也越大, 而不至于趋向僵化——这在中国古代,叫做文气。 运用文字的稠密,也就是利用一些特别精选的字眼,来达成特别的意境,像是: “咽过多少州多少郡的空寂” 也可以透过时空的压缩和景象的映衬、重叠、交替,让意象变得繁复,例如: “每次写到全台北都睡着,而李贺自唐朝醒来” 或是小孩学习作文经常被强调,结构的首尾呼应,也能因为强化了文字对读者的印象,达成密度的增加——这在中国古代,就是意象了。 他对朱自清前后期文章的评价,对英式中文的警惕,都多少暗示出他的趣味:他喜欢纯雅天然的,传统中国文人的姿态——————而台湾的许多位老先生似乎也都是如此。 怎么说呢? 这整体像一种,南朝文人气质。 魏晋南北朝时,东晋到宋齐梁陈,文人如云。因为中原衣冠南渡,贵族多在意文化素养。 所谓“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辞藻美,声律谐、隶事精、属对工。优美协调,富有古韵。后期太发达了,还流行骈文与宫体诗。 后来南宋文学,也有过类似气象。托古,抒情,优美,精致。 因为隋唐文学过于兴旺,韩愈及古文运动的诸位是反南朝文风的,所以现在对南朝文章评价不算很高。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理论成就,本身是够的。台湾的诸位先生,早年写文章,都有类似调子。读惯的人觉得古韵悠然,读不惯的便觉得文绉绉的。 对去台湾的诸位而言,退守台湾,仿佛南朝失了江北。自觉文化正朔在东南一角,必须好自郑重。所以格外优雅,格外复古。比如我一直敬佩的唐鲁孙先生,晚年在台湾写专栏怀念北平故都饮食,末了总免不了提几句“还于旧都”之类,这是当时台湾的政治正确——这些话,后来的出版稿也删了。 其他台湾作家,不至于如此激进,但这种南朝士大夫式的典雅、优美、崇古、温润、精致,算是台湾老派文学的整体风格吧。 余光中先生自己,1970年代,台湾戒严时期,反过乡土文学,还出了唐文标事件——后来他自称反对的不是乡土文学,而是工农兵文学。 所以台湾左翼诸位豪杰,又譬如李敖先生这种斗士,自然与余光中先生意见相左,看他不惯了。 自然了,文无定法,不论高低。李白觉得谢灵运牛上天了,钱钟书先生觉得谢灵运矫揉造作。视角不同,意见也不同。但说余光中先生是个书斋的南朝士大夫做派,大概应该没什么错。 说这段事,也无非借余光中先生,说说台湾诸位先生的风骨。 台湾诸位先生的文笔,有乡愁,有涵养,懂典故,知文化。他们的气质,是一种上溯历史的复古气质。所以,真回大陆来了,他们怕反而要失望的——逯耀东先生写他回大陆吃东西,摇摇头,“不是那个味道了”。 就是所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意思——哦对了,说这句话的桓温,也是个南朝人。虽然一代枭雄,依然多愁善感。南朝文章,一向如此。 所以呢,我们不必太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遗憾。 夏志清先生很早就明白这一点,他如是说过: 余光中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台湾,也不是大陆,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与兰香’的中国。 其实这句话适用台湾许多位老先生——又不止余光中先生一个人了。 余光中先生当年写杜甫: 惟有诗句,纵经胡马的乱蹄乘风,乘浪,乘络绎归客的背囊有一天,会抵达西北那片雨云下梦里少年的长安 他理想中,诗句可以穿越一切,直达梦里少年长安的。 现在,他是回到自己少年长安、李白杜甫的中华梦里去了。他对古中华的乡愁,圆满了。 也好。
余光中先生殁了,89岁。过了米寿,不可谓不久。 朋友们都开始念叨《乡愁》: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大概因为写得两岸士子血肉连心,大概入选了语文课本之故。 小时候,或者是上课不用心,或者是语文课本无载,并不太记得这段诗。 所以我印象里的余光中先生,是另一个样子。 比如《寻李白》: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从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当地一弹挑起的回音 比如十一年前那首《草堂祭杜甫》: 七律森森与古柏争高把武侯祠仰望成汉阙万世香火供一表忠贞你的一柱至今未冷如此丞相才不愧如此诗人 比如《听听那冷雨》里,蒋捷爱好者一望而知的段落。 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比起《乡愁》来,这些诗大概更接近他的气质:用典故,用意象,抒情,怀古。 他强调的弹性,是对于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蓄、融合无间的适应能力,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基础,在情境所需时,也不妨用一些欧化或文言文的句子,以及适时而出的方言或俚语,或是穿插典故。文体和语气变化多,散文弹性当然越大, 发展的可能性也越大, 而不至于趋向僵化——这在中国古代,叫做文气。 运用文字的稠密,也就是利用一些特别精选的字眼,来达成特别的意境,像是: “咽过多少州多少郡的空寂” 也可以透过时空的压缩和景象的映衬、重叠、交替,让意象变得繁复,例如: “每次写到全台北都睡着,而李贺自唐朝醒来” 或是小孩学习作文经常被强调,结构的首尾呼应,也能因为强化了文字对读者的印象,达成密度的增加——这在中国古代,就是意象了。 他对朱自清前后期文章的评价,对英式中文的警惕,都多少暗示出他的趣味:他喜欢纯雅天然的,传统中国文人的姿态——————而台湾的许多位老先生似乎也都是如此。 怎么说呢? 这整体像一种,南朝文人气质。 魏晋南北朝时,东晋到宋齐梁陈,文人如云。因为中原衣冠南渡,贵族多在意文化素养。 所谓“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辞藻美,声律谐、隶事精、属对工。优美协调,富有古韵。后期太发达了,还流行骈文与宫体诗。 后来南宋文学,也有过类似气象。托古,抒情,优美,精致。 因为隋唐文学过于兴旺,韩愈及古文运动的诸位是反南朝文风的,所以现在对南朝文章评价不算很高。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理论成就,本身是够的。台湾的诸位先生,早年写文章,都有类似调子。读惯的人觉得古韵悠然,读不惯的便觉得文绉绉的。 对去台湾的诸位而言,退守台湾,仿佛南朝失了江北。自觉文化正朔在东南一角,必须好自郑重。所以格外优雅,格外复古。比如我一直敬佩的唐鲁孙先生,晚年在台湾写专栏怀念北平故都饮食,末了总免不了提几句“还于旧都”之类,这是当时台湾的政治正确——这些话,后来的出版稿也删了。 其他台湾作家,不至于如此激进,但这种南朝士大夫式的典雅、优美、崇古、温润、精致,算是台湾老派文学的整体风格吧。 余光中先生自己,1970年代,台湾戒严时期,反过乡土文学,还出了唐文标事件——后来他自称反对的不是乡土文学,而是工农兵文学。 所以台湾左翼诸位豪杰,又譬如李敖先生这种斗士,自然与余光中先生意见相左,看他不惯了。 自然了,文无定法,不论高低。李白觉得谢灵运牛上天了,钱钟书先生觉得谢灵运矫揉造作。视角不同,意见也不同。但说余光中先生是个书斋的南朝士大夫做派,大概应该没什么错。 说这段事,也无非借余光中先生,说说台湾诸位先生的风骨。 台湾诸位先生的文笔,有乡愁,有涵养,懂典故,知文化。他们的气质,是一种上溯历史的复古气质。所以,真回大陆来了,他们怕反而要失望的——逯耀东先生写他回大陆吃东西,摇摇头,“不是那个味道了”。 就是所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意思——哦对了,说这句话的桓温,也是个南朝人。虽然一代枭雄,依然多愁善感。南朝文章,一向如此。 所以呢,我们不必太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遗憾。 夏志清先生很早就明白这一点,他如是说过: 余光中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台湾,也不是大陆,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与兰香’的中国。 其实这句话适用台湾许多位老先生——又不止余光中先生一个人了。 余光中先生当年写杜甫: 惟有诗句,纵经胡马的乱蹄乘风,乘浪,乘络绎归客的背囊有一天,会抵达西北那片雨云下梦里少年的长安 他理想中,诗句可以穿越一切,直达梦里少年长安的。 现在,他是回到自己少年长安、李白杜甫的中华梦里去了。他对古中华的乡愁,圆满了。 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