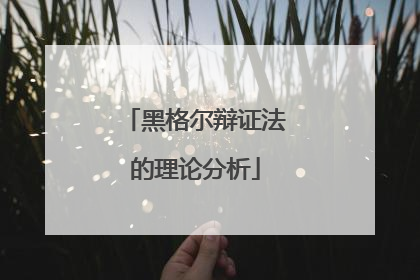黑格尔的哲学观点是什么?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绝对精神并不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东西,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都是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就是绝对精神本身。 黑格尔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展示通过自然、社会和思维体现出来的绝对精神,揭示它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实际上是在探讨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揭示二者的辩证同一。 围绕这个基本命题,黑格尔建立起令人叹为观止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主要讲述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三个阶段: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黑格尔在论述每一个概念、事物和整个体系的发展中自始至终都贯彻了这种辩证法的原则,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惊人的大胆思考之一。 黑格尔: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德语: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常缩写为G. W. F. Hegel;公元1770年8月27日—公元1831年11月14日),德国哲学家。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时代略晚于康德,是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黑格尔出生于今天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首府斯图加特;是柏林大学(今日的柏林洪堡大学)的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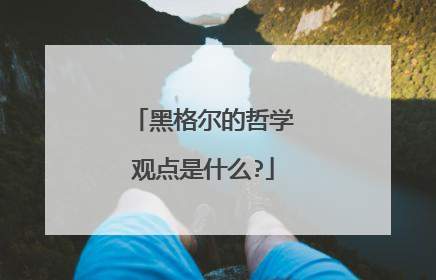
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区别?
区别: 1、思想概念不同 黑格尔辩证法其基本思想是概念的辩证发展。它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并企图揭示其内在联系,从而猜测到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 唯物辩证法以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的统一整体;辩证规律是物质世界自己运动的规律;主观辩证法或辩证的思维是客观辩证法在人类思维中的反映。 2、保守性与创造性不同 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唯物的形态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黑格尔提出的自由国家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辩证法发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扩展资料 1、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真正“合理内核”正是他吸收了培根、洛克等归纳派的思想,而用于修正笛卡尔等人的唯理派的思想。 他的辩证法是反基础主义的(笛卡尔等人的唯理派是基础主义的,即他们主张用普遍原理为知识奠基),即他认为并不能象笛卡尔等人的唯理派所说的那样,能够一次性的找到普遍公理,然后以其作为理论的基础。这表现在他的“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发展思想。 2、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发现的哲学原理。它科学地反映了关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最普遍、最深刻、最基础的规律与本质。 它指出:世界万事万物是永远运动和普遍联系的, 而运动的法则主要是依据一切事物内部的客观存在的“一分为二”的矛盾性构成的辩证运动法则,联系的纽带与方法主要是客观存在的既对立又统一为核心的一系列辩证原理组成的纽带。 这个哲学的基础是唯物论,主导则是辩证法。唯物论与辩证法互相制约、相辅相成、永远有机结合推动着这个哲学本身与社会实践亦步亦趋地一同进步着。 它不断总结社会实践新的经验验证、完善与丰富自己,同时指导社会实践快速向前发展以至无穷。它是全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最普遍的、最有效的科学武器之一。因此它是世界全人类的思想财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黑格尔辩证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唯物辩证法
1、首先,二者表现在唯物与唯心的根本对立上。马克思这一批判的第一点,就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 2、其次,二者的对立还表现在保守性与创造性上。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唯物的形态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黑格尔提出的自由国家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辩证法发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3、二者的对立,还表现在事物发展的常规逻辑与超逻辑发展的科学理解上,即社会发展的演”与跨越的理论理解上。 4、这种对立,还表现在质与量辩证发展的关系上。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只有量的积累才能引起质变。在马克思这里,跨越发展的新社会的质,是按梯度发展的。 扩展资料: 通常,人们只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来源,却相对忽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 实际上,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密切的理论渊源关系。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唯一真正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而马克思正是借助黑格尔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又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黑格尔哲学,最终实现了“经济学-哲学”的双重革命。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卡尔·马克思
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如下: 首先,二者表现在唯物与唯心的根本对立上。这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多次的“头足倒置”的批判。第一次是1843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批判的重要结论是:“理念(我们可以理解为理性——引者)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像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如果理念变为独立的主体,那么现实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情势、任性等等)在这里就会变成和它们自身不同的、非现实的、理念的客观要素。”马克思这一批判的第一点,就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是“头足倒置”的,是唯心思辨的方法。第二点是指这种思辨辩证法的内容:国家与家庭、市民社会,以及与“情势、任性”等等的关系。前者指的是国家这个一般的普遍利益与家庭、市民社会这种私人利益的关系;后者是指国家的法与个人的“情势、任性”等个人自由的关系。在这两种关系中,只有后者服从前者才是合乎理性的,才是真正的自由。以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说就是黑格尔的“自由国家”。马克思第一次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头足倒置”的批判,就是针对黑格尔式的“自由国家”的批判。马克思第四次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头足倒置”是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进行的:“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这里,不仅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而且表现为客观事物自身的辩证法与观念主体成为现实事物创造主的对立。这里既是进一步阐述辩证法的唯物性质,同时也是阐述与辩证怪论的根本对立。 其次,二者的对立还表现在保守性与创造性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是什么呢?即它的辩证历史观。黑格尔说的辩证法即历史内在的逻辑关系:“历史的职责,既然不外乎把现在和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和行动收入它的记载之中”,“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可以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理解。逻辑的依据就是历史事实,历史的事实越是详细缜密,它的逻辑性越强。在这里,可以说黑格尔是十分唯物的。但是他说理性按照概念的法则创造历史,这样,历史便成为“理性是世界的主体”创造的产物。在这里,这个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便成为最保守的东西,成为对旧事物进行辩护的辩证法论证,或合理性的逻辑说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就是这种为现实进行辩护的命题。黑格尔的“自由国家”,正是他为之辩护的对象。马克思的辩证法则不同,他的《资本论》可以说就是采取了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通过概念的逻辑: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分配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制度被否定的否定。在这里,马克思的辩证法,以科学的、唯物的形态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和逻辑的过程。但是,这里不是为现实的事物进行辩护,而是指出了它的新质的产生,即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的必然产生。在这里,黑格尔的“自由国家”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辩证法发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第三,二者的对立,还表现在事物发展的常规逻辑与超逻辑发展的科学理解上,即社会发展的“演进”与“跨越”的理论理解上。1877年,马克思的论敌米海洛夫斯基曲解《资本论》。马克思反驳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为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里说的“历史哲学”正是指黑格尔的历史理论,把《资本论》变成“历史哲学”是对马克思的“过多的侮辱”。这种“过多的侮辱”的内容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正是“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这种观点。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产生只有这样一条路才是合乎理性的。这种观点,对马克思来说,就是“过多的侮辱”。反对这种“过多的侮辱”的历史理论是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晚年指出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第一条道路是“演进”式的,是合逻辑的;而后者的发展是“跨越”式的,是超逻辑或非逻辑的。前者是“封闭式”的,是在已有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改进、改良的办法进行;而后者是在“开放式”形式上发展的,它不能按照常规逻辑来进行。这种跨越发展没有先例可寻,按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它的成就所表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正确性,也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的科学有效性。在30年的建设实践中,我们有三个理论创新,表明了这是对唯物史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这种对立,还表现在质与量辩证发展的关系上。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只有量的积累才能引起质变。在马克思这里,跨越发展的新社会的质,是按梯度发展的。结合中国的实践,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新质,它表示的是一个过程,是这个新质的不同梯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等等。对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实现,使得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又表现为三个理论创新。
马克思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虽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题域,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域中,这一问题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与现代性的问题。从这一题域出发,主张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具有紧密关联的观点,即意味着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理解为现代性思想范式中的内部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把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那么,马克思哲学显然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恩格斯、列宁、卢卡奇虽然一再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颠倒式的合理改造,但他们显然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应该属于现代性理论范式内的承继关系,即认为马克思推进和发展了黑格尔,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性哲学话语内部的延续性关系。正是这种内部延续性的理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基本理解前提。“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列宁则主张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连续。事实上,列宁提了连续性的主张。进而认为马克思的认识论的确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这就是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列宁批评了看不到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5](p212)正是基于这种连续性的理解,马克思合乎逻辑地成为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人和发展者。列宁经常用向前推进来描述这种关系。在《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中,列宁写到:“……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4](p351) “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4](p357)如此看来,无论马克思如何颠倒、批判或改造黑格尔,马克思依然在黑格尔的问题框架或理论范式中向前推进发展着黑格尔,马克思依然在传统现代性哲学的问题框架或理论范式中向前推进发展着传统现代性的理论。按着列宁的解释模式,马克思哲学只能依然是黑格尔式的哲学,只能依然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 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果然是只存在内部联系,而不存在断裂颠覆吗?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断裂?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断裂对我们把握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将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关于断裂的理解对我们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题域中,理解马克思将意味着什么呢? 阿尔杜塞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认识论断裂。”在论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时,阿尔杜塞同样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一种“认识论断裂”:“我以前曾捍卫过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思想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思想,因此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有真正的断裂或决裂。我越研究就越感觉到这个观点正确。[8](p93)基于这种认识,阿尔杜塞认为马克思创建了“一种非黑格尔的历史观;一种非黑格尔的社会结构观;一种非黑格尔的辩证法观。因此,如果这些论点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它们对于哲学具有决定性的后果:首先是拒绝古典哲学范畴的基本体系。”[8](p118)马克思所创建的这种非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与传统古典哲学思想体系完全不同的哲学。它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哲学概念,而且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阿尔杜塞为更彻底地断绝马克思与传统古典哲学的联系,将马克思所创建的哲学称之为一种哲学实践。马克思哲学并不是在与黑格尔的连续性地带产生的,而是在与黑格尔的断裂处发生的。在与黑格尔哲学的断裂处,在传统古典哲学的终结处,在传统现代性哲学的终结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才真正地呈现出来。基于这样的认识,显然不能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在黑格尔终结之后,在现代性终结之后,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我们可以将这种新范式的诞生理解为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哲学范式的开端。 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后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产生,随着后现代理论范式的生成,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理论债务终于可以得到清算。将马克思黑格尔化, 对马克思进行黑格尔式的改写或补写,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解读马克思难以摆脱的理论难题,就在于人们难以摆脱现代性理论范式的阈限,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中,呈现的后现代性意蕴。 在题为《列宁在黑格尔面前》一文中,阿尔杜塞对列宁那句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判言进行了一个吊诡式的改写:“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黑格尔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8](p148)阿尔杜塞这一理论吊诡式的改写,让我们联想起马克思的“从后思索”的思想方法,“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用马克思“从后思索”的方法,我们是否可以将阿尔杜塞吊诡式的改写进行再度的改写:“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马克思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后现代性理论范式,就不能理解马克思!”
1、首先,二者表现在唯物与唯心的根本对立上。马克思这一批判的第一点,就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 2、其次,二者的对立还表现在保守性与创造性上。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唯物的形态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黑格尔提出的自由国家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辩证法发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3、二者的对立,还表现在事物发展的常规逻辑与超逻辑发展的科学理解上,即社会发展的演”与跨越的理论理解上。 4、这种对立,还表现在质与量辩证发展的关系上。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只有量的积累才能引起质变。在马克思这里,跨越发展的新社会的质,是按梯度发展的。 扩展资料: 通常,人们只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来源,却相对忽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 实际上,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密切的理论渊源关系。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唯一真正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而马克思正是借助黑格尔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又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了黑格尔哲学,最终实现了“经济学-哲学”的双重革命。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卡尔·马克思
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如下: 首先,二者表现在唯物与唯心的根本对立上。这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多次的“头足倒置”的批判。第一次是1843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批判的重要结论是:“理念(我们可以理解为理性——引者)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像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如果理念变为独立的主体,那么现实的主体(市民社会、家庭、情势、任性等等)在这里就会变成和它们自身不同的、非现实的、理念的客观要素。”马克思这一批判的第一点,就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是“头足倒置”的,是唯心思辨的方法。第二点是指这种思辨辩证法的内容:国家与家庭、市民社会,以及与“情势、任性”等等的关系。前者指的是国家这个一般的普遍利益与家庭、市民社会这种私人利益的关系;后者是指国家的法与个人的“情势、任性”等个人自由的关系。在这两种关系中,只有后者服从前者才是合乎理性的,才是真正的自由。以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说就是黑格尔的“自由国家”。马克思第一次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头足倒置”的批判,就是针对黑格尔式的“自由国家”的批判。马克思第四次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头足倒置”是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进行的:“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这里,不仅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而且表现为客观事物自身的辩证法与观念主体成为现实事物创造主的对立。这里既是进一步阐述辩证法的唯物性质,同时也是阐述与辩证怪论的根本对立。 其次,二者的对立还表现在保守性与创造性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是什么呢?即它的辩证历史观。黑格尔说的辩证法即历史内在的逻辑关系:“历史的职责,既然不外乎把现在和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和行动收入它的记载之中”,“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可以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理解。逻辑的依据就是历史事实,历史的事实越是详细缜密,它的逻辑性越强。在这里,可以说黑格尔是十分唯物的。但是他说理性按照概念的法则创造历史,这样,历史便成为“理性是世界的主体”创造的产物。在这里,这个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便成为最保守的东西,成为对旧事物进行辩护的辩证法论证,或合理性的逻辑说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就是这种为现实进行辩护的命题。黑格尔的“自由国家”,正是他为之辩护的对象。马克思的辩证法则不同,他的《资本论》可以说就是采取了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通过概念的逻辑: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分配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制度被否定的否定。在这里,马克思的辩证法,以科学的、唯物的形态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和逻辑的过程。但是,这里不是为现实的事物进行辩护,而是指出了它的新质的产生,即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的必然产生。在这里,黑格尔的“自由国家”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辩证法发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第三,二者的对立,还表现在事物发展的常规逻辑与超逻辑发展的科学理解上,即社会发展的“演进”与“跨越”的理论理解上。1877年,马克思的论敌米海洛夫斯基曲解《资本论》。马克思反驳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为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里说的“历史哲学”正是指黑格尔的历史理论,把《资本论》变成“历史哲学”是对马克思的“过多的侮辱”。这种“过多的侮辱”的内容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正是“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这种观点。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产生只有这样一条路才是合乎理性的。这种观点,对马克思来说,就是“过多的侮辱”。反对这种“过多的侮辱”的历史理论是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晚年指出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第一条道路是“演进”式的,是合逻辑的;而后者的发展是“跨越”式的,是超逻辑或非逻辑的。前者是“封闭式”的,是在已有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改进、改良的办法进行;而后者是在“开放式”形式上发展的,它不能按照常规逻辑来进行。这种跨越发展没有先例可寻,按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它的成就所表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正确性,也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的科学有效性。在30年的建设实践中,我们有三个理论创新,表明了这是对唯物史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这种对立,还表现在质与量辩证发展的关系上。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只有量的积累才能引起质变。在马克思这里,跨越发展的新社会的质,是按梯度发展的。结合中国的实践,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新质,它表示的是一个过程,是这个新质的不同梯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等等。对三步走战略部署的实现,使得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又表现为三个理论创新。
马克思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虽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题域,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域中,这一问题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与现代性的问题。从这一题域出发,主张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具有紧密关联的观点,即意味着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理解为现代性思想范式中的内部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把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那么,马克思哲学显然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恩格斯、列宁、卢卡奇虽然一再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颠倒式的合理改造,但他们显然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应该属于现代性理论范式内的承继关系,即认为马克思推进和发展了黑格尔,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性哲学话语内部的延续性关系。正是这种内部延续性的理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基本理解前提。“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列宁则主张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连续。事实上,列宁提了连续性的主张。进而认为马克思的认识论的确源于黑格尔的《逻辑学》。这就是黑格尔化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列宁批评了看不到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者。”[5](p212)正是基于这种连续性的理解,马克思合乎逻辑地成为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人和发展者。列宁经常用向前推进来描述这种关系。在《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中,列宁写到:“……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4](p351) “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4](p357)如此看来,无论马克思如何颠倒、批判或改造黑格尔,马克思依然在黑格尔的问题框架或理论范式中向前推进发展着黑格尔,马克思依然在传统现代性哲学的问题框架或理论范式中向前推进发展着传统现代性的理论。按着列宁的解释模式,马克思哲学只能依然是黑格尔式的哲学,只能依然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 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果然是只存在内部联系,而不存在断裂颠覆吗?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断裂?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断裂对我们把握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将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关于断裂的理解对我们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题域中,理解马克思将意味着什么呢? 阿尔杜塞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认识论断裂。”在论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时,阿尔杜塞同样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一种“认识论断裂”:“我以前曾捍卫过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思想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思想,因此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有真正的断裂或决裂。我越研究就越感觉到这个观点正确。[8](p93)基于这种认识,阿尔杜塞认为马克思创建了“一种非黑格尔的历史观;一种非黑格尔的社会结构观;一种非黑格尔的辩证法观。因此,如果这些论点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它们对于哲学具有决定性的后果:首先是拒绝古典哲学范畴的基本体系。”[8](p118)马克思所创建的这种非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与传统古典哲学思想体系完全不同的哲学。它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哲学概念,而且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阿尔杜塞为更彻底地断绝马克思与传统古典哲学的联系,将马克思所创建的哲学称之为一种哲学实践。马克思哲学并不是在与黑格尔的连续性地带产生的,而是在与黑格尔的断裂处发生的。在与黑格尔哲学的断裂处,在传统古典哲学的终结处,在传统现代性哲学的终结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才真正地呈现出来。基于这样的认识,显然不能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在黑格尔终结之后,在现代性终结之后,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我们可以将这种新范式的诞生理解为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哲学范式的开端。 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后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产生,随着后现代理论范式的生成,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理论债务终于可以得到清算。将马克思黑格尔化, 对马克思进行黑格尔式的改写或补写,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解读马克思难以摆脱的理论难题,就在于人们难以摆脱现代性理论范式的阈限,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在现代性批判中,呈现的后现代性意蕴。 在题为《列宁在黑格尔面前》一文中,阿尔杜塞对列宁那句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判言进行了一个吊诡式的改写:“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黑格尔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8](p148)阿尔杜塞这一理论吊诡式的改写,让我们联想起马克思的“从后思索”的思想方法,“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用马克思“从后思索”的方法,我们是否可以将阿尔杜塞吊诡式的改写进行再度的改写:“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马克思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后现代性理论范式,就不能理解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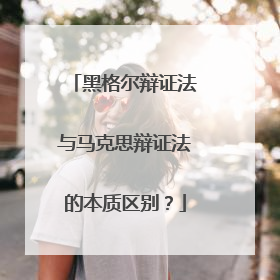
如何阐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
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真正"合理内核"正是他吸收了培根、洛克等归纳派的思想,而用于修正笛卡尔等人的唯理派的思想。他的辩证法是反基础主义的(笛卡尔等人的唯理派是基础主义的,即他们主张用普遍原理为知识奠基),即他认为并不能象笛卡尔等人的唯理派所说的那样,能够一次性的找到普遍公理,然后以其作为理论的基础。这表现在他的"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发展思想。 他的"正题-反题-合题",应该理解成"某种我们认为的普遍概念或原理--对普遍概念或原理的反对--新的普遍概念或原理",这里的普遍概念或原理只是相对意义的,而不是演绎派所说的绝对意义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是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也就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是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也就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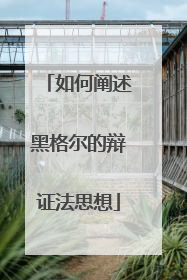
黑格尔有什么辩证法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概念的含义,他不只是把辩证法看作一种思维方法,同时认为它也是适用于一切现象的普遍原则,是一种宇宙观。他继承了哲学史上关于辩证法是揭露对象自身矛盾的思想,同时在概念矛盾运动的辩证分析中进一步阐明了所谓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本质自身的矛盾,并把这种矛盾视为支配一切事物和整个宇宙发展的普遍法则。他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在宇宙观意义上使用"辩证法"概念。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所揭示的对象本质自身的矛盾和作为发展动力的原则,不仅是普遍适用的,而且是获得其他科学知识的灵魂,是"真正的哲学方法";只有通过辩证法,才能把握哲学真理,才能真正获得其他各门科学知识。黑格尔很重视概念的运动原则,他把运动原则叫做"辩证法",又把辩证法视为研究对象本质自身的矛盾,并且试图揭示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现象的内在联系上揭示运动和发展的源泉和真实内容,这就把辩证法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关于辩证法内容的科学规定,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他把辩证法当作"思想的自我发展"强加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
黑格尔认为,宇宙自身具有能动性,人的精神世界也是宇宙“绝对精神”的呈现,同样每个实体自身也具有能动性,也可以理解为自身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可以让实体自我发展,这股力量是怎么产生的呢?
黑格尔认为,宇宙自身具有能动性,人的精神世界也是宇宙“绝对精神”的呈现,同样每个实体自身也具有能动性,也可以理解为自身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可以让实体自我发展,这股力量是怎么产生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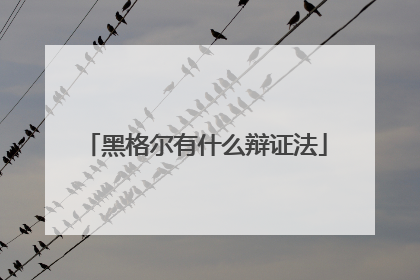
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分析
他的“正题-反题-合题”,应该理解成“某种我们认为的普遍概念或原理-—对普遍概念或原理的反对——新的普遍概念或原理”,这里的普遍概念或原理只是相对意义的,而不是演绎派所说的绝对意义的。至于绝对意义的普遍概念或原理(绝对意义的普遍概念或原理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本应该是只能通过无限步骤的辩证发展才能够达到,但黑格尔却自信的认为在他当时的德国精神里达到了——即在他的哲学里达到了,就象马克思坚定的认为资本主义之后应该是共产主义一样。这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问题,但还有一些更严重地问题。我以前曾说过一个“辩证法悖论”问题——即辩证法如何看待辩证法自身?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反普遍原理的,但是辩证法是不是普遍原理呢?显然黑格尔是作为普遍原理的,这样辩证法就要反对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是逻辑性质(概念性质、命题性质)的,他是把辩证法作为逻辑学来做的(即思辨逻辑、辩证逻辑)。他的“正题”是指演绎派和归纳派所说的“普遍概念”、“普遍命题”,只是演绎派是从绝对意义上说的,归纳派通常是从相对意义上说的,而黑格尔接受了归纳派的这种思想,通常也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说的,要不会也不会有所谓的反题了;他的反题是对正题的反对性概念、命题和事例;合题则是更高层次、更基本的普遍概念和命题。黑格尔正是用这种“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法思想,去修正传统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传统形式逻辑仅指传统演绎逻辑,而不包括归纳逻辑,因为归纳逻辑并不是“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而是“从多个小前提中归纳出大前提”。许多人所犯的错误,就是以为辩证法好像是对整个形式逻辑(包括归纳逻辑)的颠覆。其实形式逻辑是通过演绎与归纳的互补和交替运用,来弥补演绎逻辑的不足的,即,归纳1→演绎1→归纳2→演绎2→归纳3→演绎3→……。这里的“归纳1”得到的就是黑格尔的“正题1”,然后再通过“演绎1”对“正题1”进行推演,如果推演的结果与事实相符,就说明我们暂时还没有碰到“反题1”;如果推演的结果与事实不相符,就说明“反题1”出现了;然后,我们再通过“归纳2”将“正题1”与“反题1”归纳成“合题1”,而“合题1”其实可以看成新的正题,即“正题2”,这样新一轮的“辩证”(“破缺循环”)又开始了。形式逻辑正是通过归纳与演绎的互补和交替运用来弥补双方的不足的,而这里的“辩证”其实就表现为归纳与演绎的交替运用,也就是我说的“破缺循环”,而不是逻辑本身。这是早在亚里斯多德就表达了的思想。黑格尔并未遵循亚里斯多德的正确道路,而只是吸收了经验主义、归纳派的一些正确思想,用于修补笛卡尔派的唯理主义思想。因此黑格尔的哲学其实是修正后的笛卡尔的唯理主义,这是人们将黑格尔的哲学也定为唯理主义的根本原因。正因为他的思想吸收了经验主义的一些正确思想,因此他的唯理主义要比笛卡尔的更合理,更真实的反映了人类理论的动态发展过程,而不象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只是描述的人类知识的一种静态图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笛卡尔的唯理主义是基础主义的,基础(基本概念、公理)一旦建立,它就是固定不变的了,其它一切概念、原理都是从这些基本概念和公理演绎出来的,这是笛卡尔的唯理主义表现为静态的根本原因;黑格尔的唯理主义由于吸收了经验主义的一些正确成分,他认为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基础,他的辩证法是反基础主义的,因此是动态的。有许多人都说形式逻辑是静态逻辑,辩证逻辑是动态逻辑,他们的理由是形式逻辑是研究的事物的量变的,而辩证逻辑是研究的事物的质变的。这种论述是错误的、荒唐的,根本就没有弄懂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辩证法(我只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承认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之所以是动态的,是因为它是反基础主义的,或者说它的基础是动态变化的;形式逻辑之所以是静态的,是因为它是有基础的,它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静态的基础。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形式逻辑仅指演绎逻辑,而不包括归纳逻辑。形式逻辑是一个多义词,它常常专指演绎逻辑(包括传统演绎逻辑和现代演绎逻辑);也常指现代数理逻辑(现代演绎逻辑);至于作为与辩证逻辑相对的另一种逻辑的形式逻辑(即,包含传统演绎逻辑、现代演绎逻辑、传统归纳逻辑、现代归纳逻辑的逻辑),这主要是苏联、中国当年的意识形态斗争造成的,这种意义的形式逻辑在我们现在的教课书上通常直接称之谓逻辑学。由于语言的歧义性,人们常常将仅指演绎逻辑的形式逻辑的静态性,搞成了包含归纳逻辑的整个形式逻辑的静态性,这是极其错误的。事实上,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演绎逻辑的静态性是通过归纳逻辑而变为动态的,即,演绎与归纳互补、交替使用,从而使整个形式逻辑变为动态的。因此,黑格尔的经过修正后的唯理主义虽然比笛卡尔的唯理主义更正确,但是却比亚里斯多德的那种“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思想则显得错误。因此,我们应当摆脱黑格尔的“正-反-合”的动态演绎模式(辩证发展模式),尽管他的这一模式要比笛卡尔的那种静态演绎模式要更能说明一些问题,而采用亚里斯多德的“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动态交互模式,即我更详细的表述的,“归纳1→演绎1→归纳2→演绎2→归纳3→演绎3→……”。另外,造成这种“辩证”或“破缺循环”的原因,也不是客观世界所存在的男女、左右、正负、大小这样的对立属性,而是人的主客体二重性和有限性。人是客观宇宙的微小一部分,这是人的客观性特点;但是人同时又具有认识客观宇宙的能力,这是人的主观性特点。人虽然有认识客观宇宙的能力,但是人的这种能力不是无限的、超验的,而是有限的、经验的。人不可能一次性的了悟到整个宇宙的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存在所谓的人类认识的辩证发展了),而只能通过对其能感知(包括人的感官的感知和人所制造的观察工具、实验工具的感知)到的世界的归纳总结。当我们归纳出了这些能感知世界的范围内的知识和规律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演绎法对未知世界进行推演和预测。当我们的能感知的世界的范围扩大之后,这先前归纳总结的小范围内的能感知的世界的知识和规律就不一定能适用了,这就需要我们归纳出新的,更大范围的知识和规律。人的认识和知识正是这样进展的。而客观世界所存在的男女、左右、正负、大小这样的对立属性,这些都只是客观世界的一些特殊事例,客观世界还存在那些三分属性、四分属性、多分属性、无限属性的事物。我们没有理由忽视这些事物,而只关注那些二分属性的事物。而人们所描述的客观恰恰是无量主观的归结,而主观,恰恰又是无量客观的归结,这也是人学的逻辑内外联系的基础.黑格尔曾把他的逻辑学说成是“关于神的思维的科学”(《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552页),他宣称“这个内容就是上帝的展示,展示出永恒本质中的上帝在创造自然和一个有限的精神以前是怎样的”(《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1页)。黑格尔已经很坦诚的承认了,他的逻辑学是“神”学,是“上帝的展示”。而我们要做的是“人”的逻辑学。至于黑格尔说的,“上帝的展示”,我们不认为它能在有限的认知领域中达到,我们是作为最高认知目标的。黑格尔建立了那么精致的哲学,但为什么会很快被抛弃了呢?正因为他建立的是“神”学,是我们人类无法采用的,我们人类能采用的是“人”学。 其实,黑格尔的“神”学从本质上讲,仍然没有逃出培根早已指出过的演绎派的错误,就是将归纳的一些有限原理、相对原理当作了普遍原理,然后从中推导出其巍峨大厦。尽管黑格尔的辩证哲学是修正了的演绎派哲学。黑格尔是通过修正笛卡尔派的唯理主义,融入了某些经验主义的内容而建立起他的“神”学的;我们则相反,是通过修正培根、洛克派的经验主义,融入了某些唯理主义的内容而建立起我们的“人”学的。即,我在网友们的《演绎、归纳与宇宙的统一性》一文中所说的,归纳法的合理性源于客观宇宙的统一性、演绎性,以及在《最可靠的归纳法——求本原和本源归纳法》一文中所说的,合理的运用归纳法应该以一定的演绎知识体系作指导。还有人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分析法和综合法的结合。我要说的是现今的逻辑学所说的分析法和综合法一般是作为归纳法中的整理感性资料的方法。在我们现在的逻辑学书中,归纳法分为两大部分:归纳推理和一些整理感性材料的方法。而归纳推理包括简单枚举法、类比法、求因果关系五法、概率统计法等;整理感性材料的方法则包括观察、实验、比较、分类、分析、综合、统计中的选样、求平均数以及假说等。总之,我们要建立的是从洛克的作为“心灵白板但有认知能力的人”开始的,通过归纳、演绎的交互使用,坚持的是局部真理观而非整体真理观的“人”学。而不是黑格尔的“神”学,黑格尔的“神”学应该交给“上帝”去使用,而不是我们“人”能使用的。或者说,黑格尔的“神”学,是某些人的自大,将我们归纳总结的小范围的局部真理当作了绝对真理,将他自己当作了“神”。思维工具的局部有效性不等于事物本身,但也不能极端地废掉思维,这就是辩证法极化思维的问题所在,指向明月的手指头不等于月亮本身,而也不能极端地不用指头.真理不是在文字之中可以诠释的.在本体论上唯物唯心实质是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概念问题,都是绝对一元论,僵化。只有在认识论中唯物与唯心才有意义,而主观唯心恰恰是人学的方法论,客观唯物恰恰是科学的方法论,人学与科学统一于人,在人不断向内反求诸己,向外主客体一致性探险中不断提高认识,不断跳出固有偏执,在人学与科学的来回碰撞中不断彼此前进,人学引导科学价值观,科学支持拓展人学理念,而活人将引导科学与人学不断发展,人学与科学联动性归一于人。矛盾论往往将暂时的人的理解当作真实存在,实际发展一段时间,发现从前理解的矛盾原来是自己认识的肤浅所导致,所以三点论的价值在于能融合唯物与唯心于一体,通过唯物不断正,通过唯心不断反,进而正反合,完成一个新的认识高度,而人便是这个认识过程的主体,所以三点论恰恰是人学的逻辑特制,我们既需要实证,也需要理性反思,单独依靠那点都是教条的一点论,只谈他们的先后关系那是两点论,两者都谈,谈他们彼此联动归一互动的正反合认识动态阶段才是三点论。 世间一切学问归根结底都是人看世界的学问,均是指月之指,绝对性孕育于具体相对性之中,脱离具体相对性的绝对性只能谈变动,而不能谈价值,因为脱离具体相对性参照体系的价值是无法量化的,因而不能谈价值是非,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出科学与人学的微妙关系,这个关系恰恰是人类思维发展的轨迹,而这个轨迹恰恰业符合三点论的理论构架:1、第一阶段:人学完全占统治地位,科学受压制,这个时候只有反求诸己之主观唯心,而不允许在向外探寻主客体一致性方面,使用科学原则,因而导致人的思维中,只有反求诸己方法论,而缺乏向外探险主客体一致性的方法论,用人学的思维通彻一切,这就是一点论的错误所在,人学领域自然是反求诸己,而科学如果使用人学的标准必将变成使用心灵作主客体实验的错误局面,将人凌驾于物之上的错误,此刻将人神化高于物的神灵;这就是人学高于科学之神学显示阶段。2、第二阶段:科学完全占统治地位,人学受压制,这个时候只有向外探险主客体一致性的客观唯物,而不允许在向内反求诸己的领域,使用本来的人学原则,因为同样导致了人的思维中,只有主客体一致性方法论,而缺乏向内的反求诸己一致性的方法论,用科学的思维通彻一切,这就是另一个阶段一点论的错误所在,正所谓矫枉过正而已,科学领域是向外探险主客体一致性,而人学如果使用科学标准必将变成把人的思维等同僵硬的石头作纯外部记录的错误局面,将物凌驾于人之上的错误,例如我们的现在西方经济学目前就是只见物不见人的研究方式。此刻人变成物的奴隶;这就是科学高于人学之物学显示阶段。3、第三阶段:人学再起阶段,此时科学与人学共同反思,彼此依靠,彼此节制:向内反求诸己的主观唯心的人学需要向外探险主客体一致性的科学来支撑与拓展;而向外探险的主客体一致性科学又必须依赖向内反求诸己的主观唯心的人学来体验与反思;这样明显看出无论是人学还是科学均是教条的理论,只有在活人的带领下,才能在人学与科学中不端碰撞中,不断依靠彼此,将彼此不断带出固有的偏执教条的理论,使得理论不断进步;这就是科学与人学相互促进之广义人学的显示阶段。人学只有在保护人的活性价值与人权上才会限制科学,而科学也只会在现有技术成果的范围那来限制拓展人学思维的社会自然空间拓展范围。人是存在的,是活的。而活的不需要源于理论,而是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死的”只是对“活的”世界一种偏执反映。实际地球何尝不是一个活性体那。活性便是动的一种表现,而死的便是企图把这种变给教条与凝固化了。例如自然之活性便是变化,生命之活性在于变化。对自然的活性固化与教条处理便是科学,对生命之活性固化与教条的处理便是人学。所以对外的科学与对内人学这种两种凝固化的东西(认识结合),只有在活生生的人的带动下才会不断地进化,完成一次又一次“活的”抛弃“死的”的过程。 首先真理是完备性认识体系,在某个阶段而言, 世界上只有好理论,而没有“真理”理论,人学也不是“真理”,“只是研究人与内外关系的理论.本质上所有研究者都是一个大宗教就是真理教,我们坚信有一种理念存在那就是真理。科学与人学是不同两个方面的偏执性知识积累,是人对外与内探寻的知识构架,他们都是导向不断推进真理的偏执性演化,而能融合人学与科学的恰恰不是什么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不存在什么人学高过科学,或是科学高过人学的事情,它们是两个不同方面的探寻,没有那个学科高过谁的问题,对内与外两个领域,不能彼此使用彼此的标准去打压对方,科学发展不可能否定人学,人学发展不可以否定科学,人学只能为了活的人去引导与约束科学,科学也只能通过活的人去支持与修正人学。他们之间有着联动性归一的关系,人学是人对内反求诸己,科学是对外的主客体一致性体验,人学是主观唯心,科学是客观唯物,当然在人的纽带下主客观将归一为存在。人学的主观唯心需要客观唯物来实践与拓展,而科学的客观唯物需要人学的主观唯心去验证与体验。能统领人学与科学的只有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某个理论。人是变化动态的活的生命,所以科学与人学也将在这个纽带之下联动性归一为一个动态的过程:科学需要人学约束与体验,人学需要科学去拓展与支持,这便是唯物与唯心通过人完成的联动性归一的动态整体过程。本质上讲科学与人学分别是对外与对内的偏执表述,这些固化偏执恰恰需要活生生的人的推动才能不断地突破偏执,正所谓为万法唯心,实相无相。人学与科学一样只是纽带人之下的不断演化的偏执。最高的不什么是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人,即便是人,也不是真理本身与全部,只能说人本身的自性蕴含了认知宇宙的全息况味。